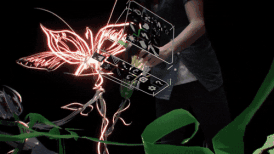导读:严歌苓其人

严歌苓
严歌苓,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是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是中国少数多产、高质、涉猎度广泛的作家。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代表作品:《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赴宴者》、《扶桑》、《穗子物语》、《天浴》、《寄居者》、《金陵十三钗》等。 被称为“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的严歌苓,小说以刚柔并济、极度的凝练语言,高度精密、不乏诙谐幽默的风格为内在依托,与其犀利多变的写作视角和叙事的艺术性成为文学评论家及学者的研究课题,在多个国家已开展严歌苓文学研讨会。其创作的“王葡萄”,“扶桑”,“多鹤”等主人物开创了中国文坛全新的文学形象。
严歌苓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精彩不输于她笔下的小说。20世纪60年代生于上海,父母离异,她和弟弟严歌平把童年留在了安徽;12岁当兵,成都习舞;20岁当过战地记者,在越自卫反击战前线,目睹死神的频繁降临;年届而立自学英语赴美留学,一边攻读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的研究生,一边赚生活费,做过餐厅服务生、带过孩子、照顾过老人等。她还曾痛苦地忍受长时间的失眠。1992年,她与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结婚,她开始像候鸟一样,春天飞到芝加哥上课,夏天飞回旧金山写作……2004年,丈夫复职派驻非洲尼日利亚,严歌苓随美国丈夫来到非洲定居,直到丈夫调离。那里有原始的民风,有很多动物,自然得让人忘掉城市攀比的生活,忘掉名牌,忘掉物质生活带给人的心理压力。严歌苓说,自己在非洲被泡洗了一遍,“我在那写了很多东西,写得开心而丰产,《一个女人的史诗》就在那写的。等我先生的任期结束,我可能还会回非洲,法语的非洲。”
作为一个女人,她经历了太多的东西,她的脚步越远,作品就越广阔,有一种悲悯的情怀。严歌苓说她之前是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但是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抛却了这种想法。她看到一百多个伤兵在病房外面等待救治,空气中弥漫着血的味道,她突然感觉人作为一个个体,是如此的脆弱,于是作品开始关照人性,以复杂的笔触描写出人性的各个方面。严歌苓能抓住一个很容易就会被我们忽略的片断演绎出荡气回肠的好看故事,她的作品看似落笔于小人物,看似只描绘他们的嬉笑怒骂,但他们的命运起伏从不会像空中楼阁般与历史大背景剥离,世事更迭不露声色、浑然天成地融会在主人公几十年的岁月中,使作品除了女性特有的细腻,还呈现出在历史中恣意纵横的磅礴大气和宽阔胸怀。
严歌苓笔下女性形象的基本类型和特征——边缘人
正如她所说“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内地的年轻女人”,她的作品中也活跃着一批中国内地的女性,她们生活在不同的时空领域,身份、性格迥异。按地域、时代来看,有跨度百年的新老移民,如扶桑、小渔、海云,在大洋彼岸演绎着自己的挣扎沉浮;有20世纪30年代河南农村的寡妇葡萄,有用一生守护爱情的女话剧演员田苏菲,她们无视身边的一场又一场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始终如一地坚守着心中的“圣地”;有《白蛇》中的孙俪坤、《雌性的草地》中牧马班的姑娘们、《天浴》中的文秀等,为读者展现出一幕幕熟悉又陌生的触目惊心的文革画面;还有生活在当代的农村女子潘巧巧,被拐卖而沦落风尘,用她短暂的悲剧的一生,演绎着处于转型期的大陆人,人性与利益、欲望的争夺……
严歌苓1980 年在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学习时,不但接受了严谨的英文写作的训练,而且开始吸收西方世界“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对“人”的价值观的透视,开始用西方文艺理论的价值判断来重新审视“东方人类”。 “这些‘中国女人’,首先有一个“中国”的身份,就带有西方社会对古老东方的‘弱族’判断,再加上一个‘女人’又是一层中国父权社会的凌越歧视,双重的‘ 压迫’感造就了她笔下更为‘弱上加弱’的女性人物形象”。不管是哪个时代的移民,还是生活在大陆的各色女子,她们的身份、思想都与主流文化的价值判断相去甚远,她们都是游走在社会主流之外的边缘人。作品中,这些女性人物,在各种文化、政治、观念的夹缝中磨砺辗转,呈现出令人震撼的丰富深邃的“人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悲悯之情。严歌苓曾说:“我到了国外之后,发现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写的。我不想控诉某个人。我只想写这样一段不寻常带有荒谬的历史运动,让我们看到一种非凡的奇怪的人性。我对人性感兴趣,而对展示人性的舞台毫无兴趣。” 她还说,“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也许在严歌苓眼中,女性更敏感,通过女性这一斑,可窥见全豹吧。
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人物有一个共性,就是她们都有一点点迟钝,有一点点缺心眼,是边缘的,弱势的。可就是边缘弱势的女性却如一滴水一样折射出丰富复杂的现实和人性。
小姨多鹤:多鹤与朱小环

小姨多鹤
《小姨多鹤》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二战进入尾声,日本战败投降,大批当年被移民来中国东北企图对中国实施长期殖民统治的普通日本国民被抛弃。十六岁的少女多鹤即为其一,在死难多艰的逃亡中,她依靠机智和对生的本能的渴望逃过了死亡,被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东北某小火车站站长的二儿子张俭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张俭的老婆朱小环因日本鬼子的惊吓而流产,从此不能生育,留下深深遗憾。国仇家恨的大背景下,日本少女多鹤的介入,使得整个家庭的关系变得暧昧和怪异。几十年下来,多鹤固执地以“整洁、较真”等品质影响着这个家庭,而朱小环等张家人则以 “随遇而安”、“凑合活着”等生活理念改变着多鹤。残酷无奈而又充满吸引力的生活因着他们善良的本性让他们活成了不能分开的一家人。
一切要从对生命的渴求开始。小说以“好死”之“忠”开篇,是那些“大和民族”代表者们,在堪称惨烈的冷静赴死的场面中践行他们的民族性,但这种极端的观念并没有在少女多鹤的心中扎根,在她心中,活着依旧是第一位的事。因此,作者从一开始就对多鹤对生命的执着和做事的顽强倔强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为后面多鹤十几年如一日的保持着自己的规则做了铺垫。虽然,生的欲望盖过了民族性的影响,但是多鹤作为一个日本女孩,内心还是残留着大和民族的特性,生死观的偏执和偶尔的偏激。“选根好绳子”、“选个干净的水塘”——在多鹤这一“好死”的冲动之下,总是有苟全“赖活”的支撑使她选择复生,尽量保持活者的体面,让“赖活”获得尊严的指望。这种矛盾这是小说的内在震撼力所在。
朱小环是张俭明媒正娶的妻子,性格泼辣,是个爱说爱笑的东北媳妇。朱小环虽然性格泼辣,打情骂俏,可对待憨厚老实的丈夫却始终是忠心耿耿。在张俭面前,她任性,好吃懒做,发起脾气来非要占了上风不可,张俭总能忍让她。张俭厚道的性格让着她,像一潭静水,活泼好动的小环风风火火,能说会道,像一阵风。他俩一静一动倒也默契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在处理与多鹤的关系上,朱小环也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气度,她让张俭与多鹤好,自己又对丈夫非常信任。即便是文革期间,张俭进了监狱,朱小环和多鹤两个女人,为了生计相互支撑。一个在家操持家务,一个在外为人做衣服,日子在两人的维系下熬了过来。所以,在张家人之间已不再是男女之情的浅薄关系,而是由骨肉亲情维系着的相互依赖。这些人物中,小环无疑是最重要也最可敬的形象。小环是这部长篇小说之所以成立的关键。是小环,把本处于险恶锋刃之地的家境、把“环境,种族,时代”叠加构成的危难生存,硬是在她的主导下变成了“生活”。在难对付的女人小脾气、聪敏的应急本领和彻骨的母爱之间,小环有着可以扩展到巨大程度的适应容量,维护家庭子女利益的强劲意志、深厚的恻隐之心,氤氲成强力无敌的人间恤暖。多鹤曾经挥之不去的自杀念头,被小环天天月月“凑合”着“混”日子的达观所感染。
《小姨多鹤》让多鹤与小环活生生地站在我们眼前。她们仿佛女人的两极,小环犀利野性,风风火火的外表下是难以言说的痛楚,多鹤沉默隐忍却固守流淌在血脉中的那份记忆。两个女人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东方女性的人格魅力和母性的伟大。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大多有这样“一根筋”的特质,她们或懵懂或练达、或静或动、或爱或恨,但最终坚持着她们的底线,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风云变幻甚至荒谬无理,她们只凭直觉按自己的道德标准“我行我素”。正是这种坚持,最终凝聚成生命的本源——顽强的生命力、善良、仁爱、守信,构成超越一切、包容一切的人间大爱,这也是文学作品令人动容的力量所在。

-
取消药品加成后,公立医院靠啥过日子?
2017-04-21 14:58:03
-
群众为啥对“意见箱”有意见?
2017-04-21 15:46:23
-
大学生缴公积金 买房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2017-04-21 15:45:17
-
24省份明日公务员省考 多地报名人数创新高
2017-04-21 15:45:17
-
【影巢双周赛有奖征集·第3期】劳动者
2017-04-20 09:5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