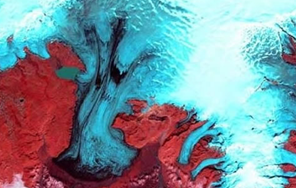5月13日继续挤兑,人数与12日差不多。为了安定人心,本来星期六半天办公,上海分行特意延长办公时间,结果挤兑人数一下子减少了400人;此后周日本来休息,也照常营业半日,结果挤兑人数不到百人。张公权此刻才算舒了一口气,记下“风潮似已平息”,但是他也没有十足把握,在目睹13日挤兑情况之下,上海分行行现金也开始减少,究竟能否支撑下去其实未必完全有把握,需联系外资银行给予帮助。
在几天的挤兑之下,上海分行虽全力应对但也几乎面临困境,毕竟挤兑就是一个信心比较的过程,在市场践踏之中,谁也不知道挤兑什么时候过去,甚至危机开始退散的时刻是压力最大的时刻,“沪行库存有200多万元现银准备,挤兑数日共兑出160余万元,同时商存款项被提取数亦达百万元”。于是,外资银行的帮助就显得分外重要。5月15日,宋汉章经理往访汇丰银行和正金银行两家外资银行寻求帮助,诸多外资银行赞成协助上海分行“至必要限度”,由各外资银行共同承担对上海分行的200万元透支借款。
当时外资银行信用良好,所以钞票得到更多认可,库存现洋颇多,所以上海分行不得不借助其帮助,而外资银行也需要市场稳定。当时势力最大的汇丰银行隐性承担了维护市场稳定的责任,汇丰银行贷款额度占据1/5,为40万元。此外,当天还决定由华俄道胜银行“出早仓”(资金一般是下午出库,早仓表示提前提出)以帮助上海分行。其实上海分行并没有动用这笔钱,但是市面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挤兑风潮旋即散去。
当然,据参与者回忆,虽然宋汉章在外资银行中颇有声望,但是交谈之中并非单凭信用,提供了上海分行行址及苏州河沿岸之堆栈、地产道契等为担保。对比之下,虽然也有呼吁帮助交通银行的声音,但是因为交通银行声誉一向不如中国银行,所以外资银行对两家中资银行的态度也是两样。
到了5月19日,风潮总算彻底平息,张公权如此记录战果,“上海中国银行之钞票信用,从此日益昭著。南京、汉口两分行鉴于上海分行措施之适当,并获当地官厅之合作,对于发行之钞票,及所收存款,照常兑付现金。影响所及,浙江、安徽、江西三省,对于中国银行在当地发行之钞票,十足使用”。
从经济上来看,上海分行已经胜利,此刻可谓“家有千金,行止不惊”,在银行加班加员应对挤兑的努力之下,挤兑风潮散去。不过,经济只是一方面,此刻又传来各方面的声援。5月16日各国驻京公使团向领事馆复电,赞同协助上海分行,但张公权当时表示挤兑风波已经平息,上海分行无须外援。
尽管此刻经济上已经不需要外援,外援的政治含义却十分清晰,对于日后的追责赢得了空间。而且,上海分行的应对也感染了不少人,原本持中立暧昧态度的机构个人也明确支持上海分行,例如上海总商会即在《申报》表示,“查中国银行准备现金甚为充足,不特发行之钞票照常兑现,即将来存款到期亦一律照付。该沪行内容之可靠、诚信而有证,惟钞票为辅助现金,全赖市面流通,斯金融不致窒塞。该沪行既备足现金、兑付以保信用,而各业商号自应一律照收”。如此趋势之下,等到袁世凯在1916年6月6日去世之后,根据李思浩回忆,执政的段祺瑞对于上海分行停兑的态度改变为“非常和缓”,承认停兑是勉强应急策略,而上海分行在租界之内,“与外国商人关系较深,停兑不易办到”。
袁世凯去世之后,大局已定,停兑风潮也意味着上海分行的完全胜利。至于“停兑令”的始作俑者梁士诒,在袁世凯去世之后被继任总统黎元洪下令通缉,继而逃亡海外,日后在一切风平浪静之后咸鱼翻身,再度卷土重来,重新入主交通银行,借助西园借款盘活交通银行——这就是闹哄哄的民国政治。
这次京钞挤兑事件之后,1921年又重演过一次。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从1916年到1923年整理京钞,在战乱中历经几个阶段才算基本完成。中国银行也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银行。1926年,中国银行吸纳的存款总额达到32 848万元,发行钞票13742万元,分别占25家重要华商银行存款总额和发行总额的35.1%和60%。
这一次胜利虽然是在张公权等人运筹帷幄之下展开,但是其中的成功也依赖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大背景。
首先,不得不承认北洋政府是一个弱势政府,这反而意味着它不会挤兑得非常霸道,北洋政府时期其实也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时期。正因如此,“停兑令”的执行并不是十分严格,南方对北洋政府的做法也表示异议,“北京政府宣布此举,系欲使中交纸币跌价,造成独立各省经济上的恐慌,北京则可席卷现金,以发军饷”。如此氛围也给予张公权等人抗命的空间。这其实是权力分散之下“东南自保”在金融领域的体现,即使秋后算账,在各界的抗争斡旋之中,最终也不了了之。
其次,这看起来是张公权的胜利,其实更是江浙财阀乃至工商界的胜利,也是市场力量的胜利。张公权最为倚重的其实是股东和工商界人士的力量。他依托于张謇、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抑卮、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人,借助股东力量公告天下,“环顾全国分行之最重要者,莫如上海一埠,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且为中外观瞻所系,故以为保住中国银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中国银行沪行决定由股东会竭力维持,将来各业企业如有损失,均由股东联合会负责向政府交涉”。
换言之,此役的胜利依赖于中国银行商股身份的强大。这也是北洋时期的一大特点,因为北洋政府财力积弱,所以官股也少,稀释之下银行内商股的比重增大,而且话语权不少,参股人员也不再类似晚清更多是官商身份,而是以商业为主。对中国银行而言,1915年大部分为官股,但是之后商股比重开始增加,1917年从17.01%升为59.29%,1921年为72.64%,1923年猛增到97.47%。根据曾担任中国银行总裁的冯耿光的回忆,中国银行几位首脑虽然性格不同,但都想把中国银行办好,也认识到要维持它的相对独立性就要尽量扩大商股权益、削弱官股力量,以免受到政局变动的影响,“北洋政府财政部因为需款应用,经常将该部持有的中国银行股票抵借款项,我们就怂恿他们陆续让售给商业银行,到北伐前夕,官股为数极少,只剩5万元了”。
最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人员地位也不可不提。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总行都在北京,但是两行在上海都设有分行,而且地位重要,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上海金融市场的中心地位,更在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半数准备金都属于两家的上海分行。根据张公权回忆,“当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之兑换券计七千余万元,现金准备约两千三百余万元。内中:中国银行存有现银三百五十万两,银币四百八十八万;交通银行存有现银六百万两,银币五百四十万元。此项现金准备之半数,属于上海中国、交通两分行”。
对比之下,交通银行的历史本身与中国银行不同。北洋政府对于交通银行成为国家银行颇有助力,而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在交通银行地位不凡,从交通银行帮办到最终担任交通银行总理。交通银行初创之时虽然获得轮、路、邮、电四项存款往来,但是在历年垫资与经营不善之下甚至亏损280万两以上,“行务停滞,几有不能支持之势”。梁士诒谋求袁世凯支持,扩大交通银行权力,为交通银行谋取到国家银行权力之后,交通银行一直在他控制之下,交通银行的经营状况却不如中国银行。当时上海《新闻报》刊登了一则“北京特别通讯”,据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总行在停止兑现、付现的院令发表前,曾致电向各地分行征询意见,交通银行分行均无意见,而中国银行各分行都不赞同,甚至有言“交通银行自杀,系属自取,中国银行陪杀,于心难安。宁可刑戳及身,不忍苟且从命”。
从全国来看,因为地域风格有异,各地对“停兑令”的执行力度和步伐也不一样。多数地区遵照实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坚决抵制也有其特殊性。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地位特殊,辛亥革命爆发后银行停业清理,然而大清银行中除了官方股份,也有商股。在商业股东出面斡旋之下,南京临时政府同意中国银行于1912年在上海(原大清银行的旧址)开业,次年才设总行于北京,固定股本总额为银元6 000万元,官商各半,由此可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地位在中国银行内外都不低。至于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其主管是交通系官员,到任时间不长,更是与商人及银行业务不熟,外资银行对于他们的态度也不同,所以不得不对“挤兑令”遵照执行。而经过这一次,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的结局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更是不同,时隔一年之后才重新营业,其总行也差点遭遇撤销。
经过这一次风波,张公权一战成名,可谓在金融界扬名立万,而且在政界与新闻界也获得不少拥护,后来梁启超邀请他担任中国银行副总裁,花费数年整顿京津地区的京钞问题,这为他日后作为江浙财阀代表支持蒋介石奠定了基础。
对抗挤兑成功不仅仅是张公权一人的功劳。据了解内情者评价,张公权交际活络,与江浙银行家、政界以及新闻界多有联系,从政经历使得他对外处理事务得力。对内而言,宋汉章在行内有实权,对外资银行有信用,而当时上海分行襄理胡氏在钱庄有地位,正是他疏通中国银行到上海钱庄市场交易,使得钱庄给予中国银行的地位是同业而不是普通客户。由于三人在不同方面“各有所长,相得益彰”,促成了中国银行在这次风潮中屹立不倒。
至于宋汉章,虽然一直以来被谈到的频率低于张公权,其实他对于中国银行的贡献也很大,其服务时间更久,资历更高。他经历了清朝、北洋、国民政府等不同朝代的中国银行。张公权说起宋汉章,评价是“静默寡言,但是朝夕相处得益亦多,美德有自奉简朴、操作勤劳、办事认真、爱惜公物、公私分明”。宋汉章日后担任中国银行总经理,1946年任四联总处理事。在孔祥熙辞职的情况下,年近80岁的宋汉章还在1948年4月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目的也是为了保持中国银行独立。1949年他辞职去巴西,1968年在香港去世,享年96岁。宋汉章的一生,除了这次对抗北洋政府,还曾经对军阀陈其美、蒋介石的借款要求强硬回应,有人甚至将他称为中国银行的精神领袖。至于胡氏,曾有上海钱庄经历,张公权说他对于钱庄历史业务尤其熟悉,与之谈论市面情况增加知识不少。
在“抗兑令”中,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在致电国务院、财政部和中国银行总行的电报中提到,“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存,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之后,财政信用一劫不复。沪上中国银行由股东决议,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千万合力主持,饬中行遵办,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为人民留一线生机,幸甚”。日后发展也多少印证这些银行家的当年期待,虽然政局变动,中国银行仍旧得到长足发展,中国银行存款总数1917年年底为1.4亿元,1928年年底为3.8亿元;钞票发行额1917年年底为7 000万元,1928年年底为1.7亿元。1928年年底,全国银行发行总数为2.9亿元,中国银行发行总数约占一半;全国各银行活期、定期存款总数为9.8亿元,中国银行存款总数约占4成。中国银行的地位不仅在全国卓越,在上海等地甚至高于官方的中央银行,“1934年年底,全行存款总数达5亿余元,各项放款为4亿余元,均较中央银行多一倍许,发行总数为2亿余元,较中央银行多两倍半”a。
“京钞风潮”与“抗兑令”背后,不仅折射出中国银行业与银行家转瞬即逝的黄金时代,也暗示了一个教训:政府无信用情况下,民众往往更偏好白银之类的金属货币,金属货币的存在其实天然对于纸币的通胀是一个束缚,若非如此,不受控制地发行纸币必然引起通胀,引发金融动荡。可惜这一教训并不被后来的国民政府所接受,在白银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纸币的效应被放大再放大,民国政府在通胀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直至灭亡。

-
 前11个月 河北国企利润同比增长83河北国企利润同比增长83.2%科技人工智能2016-12-24 12
前11个月 河北国企利润同比增长83河北国企利润同比增长83.2%科技人工智能2016-12-24 12 -
前11个科技人工智能2016-12-24 12
-
前11个月 河北国企利润同比增长83河北国企利润同比增长83河北国企利润同比增长83河北国企利润同比增长83.2%科技人工智能2016-12-24 12
-
2017年“我向总理说句话”建言征集活动
2017-02-21 09:55:26
-
“国家账本”邀您过目,哪笔花销你最关注?
2017-03-06 13:49:56
-
[两会单车日记]一辆有故事的共享单车
2017-03-06 13:49:35
-
扶贫攻坚,你有哪些锦囊妙计?
2017-03-09 10:56:21
-
古往今来几时“休”:看中国“休假制度”变迁
2017-03-09 10:5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