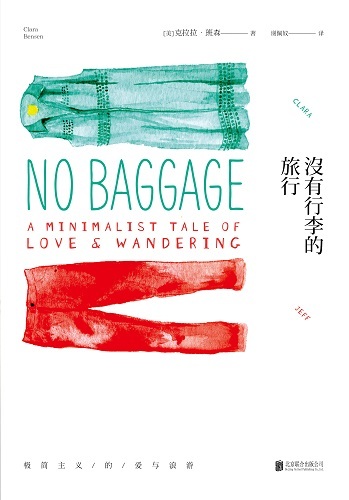
(本文摘自《没有行李的旅行》,[美]克拉拉·班森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所以,你真的了解这个要跟你一起远走高飞的家伙吗?”
詹米从照后镜中看着我,眼睛藏在墨镜后面,但听得出来他在逗我。 要跟我远走高飞的“家伙”,就是他的大学室友杰夫,这会儿正坐在他旁边的副驾驶座上。我们三人坐在一辆富豪汽车里,在休斯敦水泥迷宫似的早晨车流中穿梭,往乔治布什洲际机场前进。我跟杰夫已经订好班机。
“别闹了,詹米!”杰夫含着微笑说,像个妈妈一边斥责调皮捣蛋的孩子,一边忍住不笑。
“我只是要说,”詹米仍不死心,“难得有人有‘荣幸’跟你出国旅行,也该让人家知道自己上了什么贼船。”他一手放开方向盘,用手肘轻戳杰夫,接着又回头看看照后镜里的我,等着我回答。你真的了解这个家伙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四两拨千斤:“有什么我该知道的吗?”
“你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詹米开玩笑地说,“我敢说,他一定‘忘了’提他拔掉手上的点滴、夹着尾巴逃出巴黎医院的事,那天刚好是巴士底日隔天的早上。妈呀,这家伙穿着纸睡衣跑上走廊,就是那种会露出屁股的病人服,你知道吧?连衣服都还没换下来,他就冲出医院,订了机票,立马跟法国说拜拜。”
“别说了,詹米!”杰夫吼他,假装听不下去,“都二十年前的事了,当年我们的毛都还没长齐!”
“是吗?”詹米耸耸肩,“只能说,接下来三个礼拜,我的念珠可有的忙了。”
我坐在后座,玩着裙摆上的花边。窗外的地平线那头,在半完成的建筑和空旷的水泥停车场后面,一排小小的飞机正要升上雾蒙蒙的日出天际。起飞的时间越来越近,再过几个小时,我的——我们的——飞机就会在跑道上滑行。这是个好问题!我真的了解这个坐在我旁边一起等待机轮从跑道上升起的男人吗?
说了解也对,说不了解也对。
我知道杰夫是理科教授,第六代得州人,一双眼睛闪着狂野的光芒。我知道我第一次看见他,心里不禁想“哈,原来是你”,简直是巧遇老友。我知道我们的关系在一巡龙舌兰之后,就变成眼花缭乱、惊险刺激的马戏团表演。我知道他喜欢在巧克力上撒海盐,还知道他结婚六年、分居两年,有个棕色眼睛亮晶晶的五岁女儿。我知道他很特立独行,就像冬天不往南飞、偏往北飞的候鸟。我知道他超爱惹是生非,但听到饶舌天王图派克(2Pac)的《亲爱的妈妈》(Dear Mama)就会掉眼泪,偶尔还会停下车,温柔地把路上的死猫移到路边。他是个内心柔软的捣蛋鬼——如果这两种特质可以同时存在的话。
但是,我真的了解他吗?很难说。你对在网络上认识没多久的人能有多了解?
也许认识的时间和场合也没那么重要。在网络上用电子邮件口无遮拦地打情骂俏几周之后(像打网球咻咻咻地一来一往),杰夫好不容易突破我这个影子写手的含蓄矜持。很难得,算他厉害。先是在线说说笑笑,一周后,我们自然而然就约了见面,但感觉不像初次会晤,反而像久别重逢。
两个天差地别的人,没想到竟然一拍即合!我人生的前十三年都在俄勒冈州波特兰这个多雨的城市度过。我们一家七口(爸妈、五个小孩——四女一男)住在提拉穆克街(此名源于西北太平洋的原住民部落)一栋维多利亚风格的百年老宅中,家里只有一间浴室。我爸妈一方面因为信仰、一方面因为教育,把我们留在家中自学(当地中学在我的想象中,是个散落着保险套和针头的邪恶巢穴)。我妈虽然是虔诚教徒,却也很注重我们的学业和社会竞争力,所以我们一点也不像传说中穿着长裙和吊带裤、不准出门约会和跳舞的基督教自学小孩。纽约双子星大楼倒塌的那年夏天,我们搬到得州的沃思堡,我就在这座牛仔城长大成人。这里的暴风雨可以把天空变成诡谲的菠菜绿,把草丛里的蛇吓得惊惶乱窜;这里的人喜欢橄榄球的程度,几乎可比对耶稣的崇敬。
而杰夫是土生土长的得州小孩。他跟三个姐妹从小在休斯敦和圣安东尼奥长大,离这里以南四小时的车程。夏天,他都到得州丘陵区(他的高祖父在那里盖了一栋小木屋)钓鱼、寻找阿帕切人留下的箭头。大学是他比较保守的年代,读的是得州农工大学,还是个嚼着烟草的共和党青年党员,疯起来可以把乡下舞池给掀了。
他的个性也很得州,热情又奔放。小时候他曾跟医生坦承,他心里最大的恐惧不是狼蛛或坏人,而是有一天会人体自燃(就像《摇滚万岁》那部片里的鼓手一样,因为豪情万丈的独奏表演,化为一阵烟雾)。杰夫是人肉导电体,每个认识他的人都会被他电到(而且他交游广阔,五湖四海皆朋友)。一拍即合、刺激冒险、轰动场面,还有闪亮的彩色图片最合他胃口。
他的字典里没有“低调”两个字;我跟这两个字却是好朋友。我们家的人都内向到极点(包括我在内)。如果说我是敏感内向的“阴”,杰夫就是热情好动的“阳”。我的衣柜都是麻灰色或米色的毛衣,他的衣柜则挂满颜色鲜艳的卡其裤和亮晶晶的袜子。我的盆栽和朋友的比例是十比一,就算整天不说话也怡然自得。
刚开始交往的几周,我们做的性向测验证实了我的怀疑:我们的个性刚好是两个极端,杰夫是可以迷倒众生的超级行动派,而我是低调的梦想家,一口气把米切纳长达三十三小时的有声书《波兰》(Poland)听完,也不会打瞌睡。
有时候,旁人会把我的内向误以为是高傲,但杰夫不同。打从第一次约会他就表明,他对我这种安静思考的能力心存敬畏。总之,他对待我的安静内向的方式,就像对待需要仔细观察的外星生物。
“我有点好奇,今天你开口说了几句话?”我们见面后一个礼拜,他问我,当时我们坐在一家昏暗的酒吧里喝啤酒。
“喝这杯啤酒之前吗?呃,今天早上我跟服务生点了一杯咖啡。”我说,屈指算了算,“所以至少一句吧。”
他难以置信地摇摇头,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草草记下人类学的田野笔记。“那这里呢?”他敲敲我的头,露出顽皮的微笑。
“多到我希望有开关可以把它切掉。”我说。确实一向如此。
我们就像太阳与月亮。然而,2013年4月5日晚上7点52分我们见面的那一刻,一切都不重要了。那刚好是日落的时刻,不过他传给我碰面时间时,我并不知道。除了时间,他还传来一组坐标(30.2747°N, 97.9406°W),还有一张嵌在水泥砖里的红土星星的照片。他写道:到星星这里找我。照片中的星星很朴素,五个红土星芒包围着一个宝蓝色正方形,中间有道裂痕。不过,外表朴素当然是骗人的。我输入坐标就发现,杰夫的红土星星嵌在奥斯汀天际中最壮观的一栋建筑前──得州议会大厦。
晚上7点20分,我检查过口红,练习过但愿会迷死人的微笑,便走出我的小小套房。得州议会大厦的粉红色花岗岩圆顶通常要走上三十分钟才会到,但那天晚上我只花二十分钟就到了。我在人行道上迈着大步疾走,想甩掉紧张的感觉。之所以紧张,不是因为一般网友见面会担心的事,比如杰夫是个秃头的C++程序设计师,或是小孩一卡车的有妇之夫,还是喜欢性感皮衣女郎或收集了1993年以来每一款豆豆娃的怪咖,而是因为心里隐隐有种预感:有个超大星体正高速飞向议会大厦,即将把我从原来的轨道扫落。
我比杰夫早到星星那里,一直等到议会街的街灯亮起来,他才出现。当时我站在巨大圆顶的正门阶梯下等他,只见一条淡黄色裤子朝着我走过来。他直接走向星星,大胆地凑上前亲我的脸颊。一切就从那里开始。一个无所不包的小世界,有淡黄色的长裤、红土星星、呈现完美弧形的圆顶,甚至伴随着四月阳光的落日余晖。
